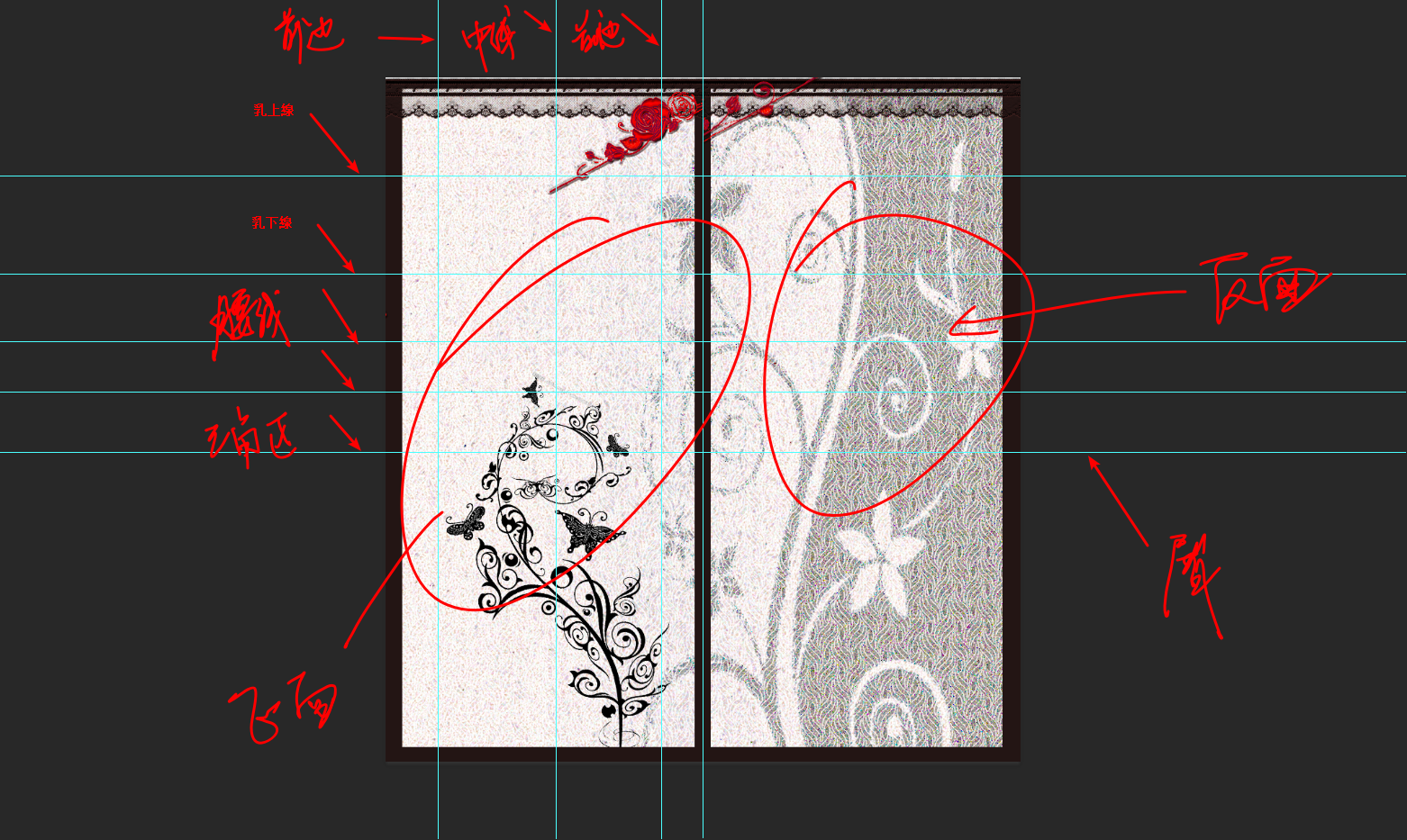我在楞垛上,沐浴着寒风,感受到肆意吹拂的寒意。
我的工作是搬运木材,一根一根地移动着那些沉重的圆木。
而这一天,我媳妇云芝却找上门来,站在楞垛下,跳着脚,大声咒骂着我:“泉小全,你这个木头,家里没有足够的燃料,你竟然要烧我的大腿!”我茫然地看着楞垛下的她,就像是陌生人一样。
她的声音被寒风吹得模糊不清,我几乎听不清她在说什么。
我耳背如同沉睡的湖水,只能看到她的嘴巴一张一合,头发像被风撕扯的鸟巢一般凌乱。
她身穿一袭红色碎花的棉袄,在一群黑衣戴狗皮帽的汉子中显得格外鲜艳。
雪花开始飘落,楞场上的风刮得更加猛烈,使人难以辨别楞垛上和楞垛下的人影。
云芝在楞垛下跳脚咒骂,引来了旁边一些汉子的轻笑。
特别是那句“你竟然要烧我的大腿”,让一些汉子心生不正当的幻想。
每个人都知道云芝的大腿又粗又壮,而她的脸却白得如同白桦树皮一般。
风刮得楞垛上的我脸颊生疼,仿佛被无情的巴掌拍打。
我沉重地叹了口气,放下手中的搬运工具,蹲下身子。
我摘下露出破洞的手套,用双手揉搓起来。
那黑色粗糙的手掌上布满裂缝,指尖处甚至还有坚硬的老茧。
从脚下冒出的风夹带着雪花,蜿蜒而过,像蛇一样在我身边蜿蜒。
“泉小全,你这个木头,我嫁给你简直是倒了八辈子霉!”云芝的声音渐渐停止,被门卫的劝解声音所取代。
那个穿着红色碎花棉袄的云芝终于离开了。
楞垛上,又恢复了搬运圆木的嘈杂声,传动台上的铁滑轮链开始滚动,发出嗡嗡声。
我重新搬动起圆木,但动作变得迟缓而机械。
有一根圆木松动滚下,险些砸到我的脚。
下班后,其他工人们纷纷赶到传动带东边,从一堆堆木头中挑选出一截,夹到自行车的后座上,用带有铁丝钩的皮带牢固地固定住。
然后,三三两两地朝着贮木场的大门走去。
我推着那辆又破旧又笨重的自行车,穿过场门口。
一个矮个子的门卫从门卫房里探出头来,看着我自行车后面鼓鼓囊囊的麻袋,嘴里嘟哝了一句:“真是一块榆木疙瘩呀。
”然后又缩回头去,我这个笨人沐浴着雪末儿,推着白色的自行车,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
我是来替我父亲上班的。
我父亲曾经在楞场上工作了一辈子,做着搬运木材的工作,直到有一天,一节装满木材的铁皮车把他的一只脚轧断了。
我借用了他工伤的名义来到了这个贮木场,每天要工作十个小时。
我右耳有些失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一直在家里闲着。
刚开始来场里工作的时候,他们原本要安排我在场部烧水打杂,但在我刚刚被领到楞场上的那一天,发生了一场惊险的意外。
楞场上的人突然遇到了一个滑垛,垛顶上的圆木像野马一样横冲直撞,众人四散奔逃。
而我却站在原地,不知是因为没有听见,还是被吓呆了。
看着圆木如野兽一般滚下,我正在用压脚子搬动着松垛的人。
一根松木正追着我狂奔,我看着它迅速接近,将压脚子斜插在横枕木下,圆木咚地一下被卡住了!大家都目瞪口呆。
“这是谁?”楞场上的工人们惊讶不已。
“我不认识……没见过。
”被问到的人摇摇头。
的确,很少有人认识我,这个场部新来的工人,我性格木讷,不太爱和人说话,最多只会嘴里咧嘴“嘿嘿”地笑笑。
我外表粗糙,笨手笨脚,经常被人嘲笑:“看看你,茶炉里的水要烧得这么久吗……”茶炉上的汽嘴已经响了好久,我却没有听见。
“看看你的手,这么黑,不会多洗几遍吗……”我给人倒水,又有人这样说。
我每天上班后总是会反复洗手,但那双粗糙的手似乎永远无法变得干净,指甲缝里总是残留着煤灰渣,手掌上的皮肤也充满了粗糙的纹路。
每当有人这样说我的时候,我就会低下头,不知道把双手放在哪里,感到有些不知所措,木讷地站在那里。
人们给我取了个绰号,“榆木疙瘩”,我开始听到了这个名字,也默默地接受了。
后来,就是那位被我救下的工段长告诉场长,要将我调到他们段里,成为一名“倒楞—厂”的工人。
我很喜欢这份工作,这样我就不必在场部做杂活,不必看别人的脸色。
站在楞垛上,我不再那么笨拙,我的身体充满了力量,每一次动作都如同指挥一支乐队,让圆木有条不紊地滚下来。
段长站在下面看着,摇着头说:“这个泉小全,真是个奇怪的家伙。
”我每天早上都会很早起床,天还没有亮透,屋子里充斥着寒冷的气息,每一口呼吸都感到寒冷。
黄泥墙角上挂着厚厚的白霜,我摸索着穿上衣服,穿上鞋子。
云芝蜷缩在被子里,一动不动,寒冷已经让她把头都藏在被子里。
五岁的枝丫睡在床上,被子包得严严实实。
我一夜中要多次起床,去外屋往炉子里添加锯末子。
火炕的灶坑也要被我填满,炕头要被我烧得滚烫。
枝丫有时候会踢开被角,我每次都会重新帮她盖好。
云芝睡在床中间,我躺在床梢,她的脚有时也会踢开被子,我每次都会重新为她盖好。
但有两次我没有盖好,看着云芝露出的光脚,我的血液突然上涌。
我试图伸出脚,轻轻触碰她光滑的脚背,她察觉后,踢开我的脚。
云芝喃喃自语:“拿开,凉死了。
”我脚缩回自己的被子里,狠狠掐了自己的大腿一下。
烧锯末子的火热得很快,也很快冷却。
在冬天,云芝很少会和我发生性关系。
听着锯末子在炉子和灶坑里呼呼燃烧,我的身体却时而涌动着一阵血液,但我仍规规矩矩地躺在床上,仿佛一只老猫一样。
过了大约两个时辰,屋子渐渐冷却,我再次起床,走到外屋去添锯末子。
淆晨醒来的时候,屋子已经完全冷透了,爬出被窝后,屋里冷得宛如冰窖一般。
我摸索着走下床,穿过外屋,发现炉子的火已经完全熄灭,灶坑里的火也早已熄灭。
我重新往炉膛里倒入锯末子,点燃炉子,用桦树皮引火。
等炉子发出呼呼的声音后,我再往灶坑里加上锯末子,并用白桦树皮点火。
渐渐地,冷冷的室内和外面逐渐变得温暖起来。
完成这些后,我又给锅里加水,盖上木制锅盖,供女人和枝丫用来洗脸。
我自己从不用热水洗脸,只用冷水,因为这样早晨出门能更好地抵抗寒冷。
我打开房门,发出一声吱呀的声音,准备出门,但冰冷的寒气差点让我打了个寒战!浓密的寒雾从门缝中涌入,我赶紧把房门关好。
窗户上的防寒毡都挂满了白霜,我走到自行车旁,用手拍打着车把,然后推着自行车吱呀吱呀地上班去了。
回头望着家里房顶上冒出的白烟,尽管我的脸上被寒气刺痛,但心里却感到一丝满足。
我们在北山街的这座平房,总是第一个冒出炉子烟的家。
“泉小全,昨晚你媳妇让没让你烧(骚)她的大腿呀。
”有人见到我就开始嘻嘻笑着调侃我,自从我媳妇曾经在场里闹过我后。
我木讷地看着那个开玩笑的人,仿佛不知道该怎么回应,然后转身走到一边开始工作。
“泉小全,你的压脚子到底好使不好使呀,怎么这么久没见有什么动静呢……”又有人这样嘻嘻笑着跟我说。
我站在一边,一个人撬起一根粗大的圆木,它在我的力量下滚下来,雪末飞扬,覆盖住了下面几个人的笑声。
他们都吃惊地瞪大了眼睛,看着我表现出的强大力量。
工段上的人都知道,枝丫不是我和云芝的孩子。
云芝嫁给我时,她已经怀着别人的孩子,但她家急于把她嫁出去。
有传言说孩子的父亲是一个从上海返城的知青。
云芝嫁给我时,她哭哭啼啼,不知是为了自己的委屈,还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的委屈。
在婚前,云芝跟我说,只要我娶她,就必须答应她把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
我点了点头,答应了她的要求。
媒人也告诉了云芝的家人,虽然我有一只耳朵失聪,但我有一份工作。
云芝的家人也不再计较我家庭里一个瘸子和一个聋子的情况,反正结婚后我们是分开住的。
结婚后,我和云芝分居,除了在从场里往家里驮木头儿这件事上,我没有听云芝的。
云芝羡慕别人家院子里堆满整齐的木头儿,总是在我面前唠唠叨叨。
我虽然耳背,但也就默默地听着云芝的抱怨。
我坚持不往家里驮泉小全头儿,因为我记得我父亲曾告诫我,多作恶多招报应。
贮木场里有人表扬我,说我是个爱工作的同志,不在工作时间私自往家里驮泉小全头儿。
但这个决定却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和不满。
不久后,因争夺一个适合的泉小全头儿,两名工人在斗争中一人被油锯截去了一根手指。
厂里随后明令禁止工人下班往家驮泉小全头儿。
大家将这也归咎于我。
我每天依然到贮木场里来,走到传动带铁轱辘链上转转,又走到空空的楞场上转了转,那楞场上只剩下几根空空的枕木了。
这么大的楞场咋说空就空了呢?我有点想不明白,我坐在那根有点朽烂的枕木上有点发呆地想。
天气暖和了,空荡荡的楞场里散发出一股好闻的松树皮和锯末子的味道,我喜欢闻这股味道。
我常常坐在那里发呆,一坐就是一天。
云芝又来过贮木场找过两次我,云芝叫我跟着人上山去采山野菜,我像没有听到一样坐在那里没动。
这个女人又跳着脚骂我是死榆木疙瘩,贮木场都完了,我还守在这里有什么用?没有了看热闹的人,这个张牙舞爪的女人骂了一阵就觉得乏味了,悻悻地离开了。
春天两只黄蝴蝶在追着她的背影飞,一直走到场大门口上看不见了。
后来这个女人自己跟着人家上山采山野菜和山花椒梗去了。
没有活儿干的我蹲坐在那里,背显得更驼了。
我每天到场里来都巡视一遍。
那几个留守看场的人则坐在门卫房里打扑克。
有一天上午,贮木场里进来了几个偷枕木的人,他们将楞垛地下的枕木都挖了出来,准备抬到场外去。
我上前抱住一根枕木,不肯让他们抬走。
那几个人不听劝阻,上来就对我进行了殴打,但我死死地抱住枕木不肯放手。
我鼻子被打得流血,腿和腰也受了重伤,但那根圆木枕木就像黏在我身上一样,怎么也分不开。
后来,木板房里的几个人听到了声响,走出来将那群人赶散。
“这么一根破枕木,偷走就偷走吧,你要是被打伤住院了,这破场子可连住院费都出不起。
”那几个人嘟嘟嚷嚷,又义无反顾地回到了门卫房里继续打扑克。
我一瘸一拐地回家,鼻血仍然从两只粗大的鼻孔里流出,在温热明亮的阳光下显得鲜红。
那些出去找工作的人都挣到了工资,而那些上山采山野菜的人也挣到了钱,只有看场的人依然无法拿到工资,因为场里没有足够的钱支付他们的工资,只能发白条子。
于是,那几个看场的人决定将传动带台上的铁轱辘链拆卸下来,当作废铁卖掉。
他们都背着我在夜里进行了这个计划。
场里传动带台上的铁轱辘链被人拆卸后,我的工资被扣了,尽管这只是白条子,但那几个人却毫不在乎。
他们依旧在木板房里打扑克,嘴里吐着烟圈,哼着电影插曲。
我渐渐变得沉默寡言,每天只是默默地来到场里,坐在那里不再与任何人交流。
有时候,我坐在那里,双手垂落,目光茫然地凝视着远方,心不在焉。
云芝自从春天跟人上山采山野菜后,几乎不再回家。
街坊邻居开始传播一些流言蜚语,我开始注意到,每次走在街上,邻居们都指指点点,窃窃私语,传闻与我有关。
有一位女邻居曾好心地拉住我,耳语着让我不要让云芝再跟其他人上山。
我凝望着这位女邻居,试图听清她到底在说什么,但她突然停了下来。
每天晚上,我回到家,发现冷锅冷灶,枝丫蜷缩在床上哭泣。
我笨拙地为枝丫做饭,家里只有一些苞米面,我煮了苞米面粥,又做了苞米面饼贴在锅边。
大饼上留下了我的粗大手指的印记,枝丫吃过后停止了哭泣,入睡了。
她的脸上仍然挂着两道泪痕,如同虫子一般。
然而,我却无法入睡。
以前,每晚在入睡前,我习惯听云芝责骂的声音,现在没有了她的责骂声,我感到孤独,无法入眠。
房子四周空荡荡的,让我感到更加寂寞。
“泉小全,媳妇说的不能不听……” 这是我母亲曾经对我说的话。
“泉小全,你要听话,要听你媳妇的话……” 这是我父亲告诫我的话。
“唉!”我抓住头发,用拳头重重地敲打着自己的脑袋,我后悔没有听从云芝的建议,没有跟着她去采山野菜。
如果我去了,云芝就不会跟其他人上山了。
我经常整夜都睁着眼睛。
云芝回来后,她带回了一种罕见的山云芝植物,然后将它卖给了前来收购山货的山外客。
用卖山云芝得到的钱,云芝开始改变自己的形象,穿上鲜艳的衣物,扭动着身姿自信地走在北山街上,嘴里还吐着瓜子皮,嘴唇抹上了鲜艳的口红。
“这种女人真放荡!”街坊邻居在幕帘后议论纷纷。
一些采山的人听说那株山云芝是其他采山者发现后让给云芝的,也有人说是云芝在夜晚偷偷钻进那名发现山云芝的汉子搭建的临时棚屋,用来交换的。
无论如何,街坊邻居们纷纷议论纷纷,甚至有时候当着我的面议论,明知我听不见,但他们也不在乎,因为他们知道我已经无法回应云芝。
看到我每天驼背低头,默默地来到贮木场,邻居们会在心里感到遗憾,对我这个泉小全不禁摇摇头:这个泉小全……自从云芝带回了山云芝之后,她不再上山。
她每天都打扮得漂亮,自信地走在北山街上。
北山街两旁住着原来贮木场的职工家属,两旁的松木皮板障子在夏天被烈日暴晒,常常散发出松节油的气味,这种气味有时会盖过菜园子里的茅坑气味。
直到再也听不到那些女人的议论声,云芝才不再招摇地走动。
那条不太长的黄土街道上,没有云芝的身影,也没有女人们的嘈杂声,生活变得安静了些。
有一天晚上,我回家发现云芝不在了。
我打开木柜箱,发现她的衣服也不见了,而枝丫坐在床上哭泣。
我去云芝的娘家打听,但娘家告诉我云芝没有回去。
我才知道云芝离开了我,抛下了枝丫。
我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那一夜,我几乎走遍了林业局小镇,寻找她的踪迹,询问了云芝以前曾经搭伴上山的人,但没有找到云芝。
最后,我失望地回到家。
街坊邻居们开始传言,说云芝跟山外客跑了,有人看到云芝经常围着山外客打听外面的事情,还找山外客带东西。
还有人说,云芝坐火车去找了她以前在上海认识的知青朋友。
对于后一种说法,也有人反驳说,如果她是要找那个知青朋友,为什么不带着枝丫一起走呢?毕竟枝丫是他们的亲生女儿。
有了这些传言,街坊邻居们不再当着我的面议论,他们知道我听不见,但他们也不在乎。
我继续每天去贮木场上班,带着枝丫去,把她放在阳光下的锯末堆上玩耍。
有几个闲人看到后,问我:“泉小全,你还来这里干嘛?你老婆都跑了,你和孩子还留在这里干什么?”我茫然地看着他们,然后看了看头顶刺眼的太阳,仿佛没有听到他们的话,继续走到另一个地方去查看。
那几个人退回到门卫木刻楞房里继续打牌。
夜晚在雨水的洗涤下,楞场里弥漫着一股腐朽的木屑气味。
我在场里转了一圈,蹲坐在一根枕木上,发现自己两天没来,传动带台上的铁轱辘链又减少了几截。
我呆呆地蹲在那里,把目光从传动台上移到传动台下,突然发现在传动台下的阴凉处,锯末子上生长出两丛像耳朵一样的植物,黑黑的,难道是黑木耳?我的眼神呆滞地跳动了几次。
我想起以前一个收山货的山外客告诉云芝用锯末子养殖木耳的事情,云芝说她闻够了锯末子的味道,甚至把那包木耳菌随意丢在墙角。
下班后,我又开始往家里驮锯末子,白行车的前梁上装着枝丫,后座上则放着装锯末子的麻袋。
没过多久,我的家里的房顶、屋里的炕梢、地上和院子的背阴处,都铺满了银灰色的陈锯末子,屋内和院子弥漫着浓烈的锯末子味道。
再过了几天,经过两场雨水后,那些锯末子上开始长出黑黑的木耳。
先是被邻居发现,消息迅速传遍了街坊邻居之间,吸引了一些收购木耳的人前来,卖了好价钱。
于是,邻居们纷纷效仿我去贮木场弄锯末子,大人和孩子们拿着麻袋、洗衣盆纷纷涌向贮木场大门。
但不幸的是,贮木场的大门已经关闭,因为贮木场被一家木器厂收购,正准备建厂房,我和那几个看场的人也被赶回了家。
离开前,那几个看场的人还偷走了传动带台上最后一段铁滑轮链。
但是,我并没有放弃,我在家里努力养殖木耳。
光着膀子,我满头大汗地把锯末子装进一个个白桦树皮筒里,堆满了院子、屋顶等各个角落。
这些白桦树皮筒是我从山上割下来的,正如那位收购木耳的人告诉我的,用桦树皮筒装锯末子不容易腐烂,而且可以反复使用多次。
枝丫也在帮我忙,她爬在锯末子堆上,用小手抓着锯末子往白桦皮筒里灌,就像幼儿园的孩子在玩沙滩堆积木一样,她的脸和头上都被锯末子粘满,但她依然充满了乐趣。
夜幕降临,满满一院子的白桦树皮筒装满了锯末子,就像一个火炕一样热。
我一个人蹲在院子里,凝视着那些白桦树皮筒装满锯末子的景象,头顶上的月光洒在我的头上和那些白桦皮筒上,仿佛看见这些白桦皮筒中长出了黑黑的木耳,它们茂密而巨大,就像山云芝一样……我期待着院子门后会响起声音,云芝会走进来。
我坚信云芝一定会回来……我就这样靠在一个从偏厦子倒出来用来装锯末子的麻袋上,闭上眼睡着了,嘴巴咧开,皱纹沟里还沾着几粒锯末子粒。
总结: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了泉小全的生活经历了巨大的变故。
他和云芝结婚后,过着平凡的生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婚姻陷入了困境。
云芝的离开让泉小全陷入了孤独和挣扎中。
尽管生活变得艰难,泉小全没有放弃,而是积极寻找生计的机会。
他在贮木场找到了一份工作,然后通过种植木耳来增加家庭的收入。
这个改变不仅展示了泉小全的坚韧和适应能力,还传达了希望和重新开始的可能性。
故事中的木耳象征着希望和新生活的机会。
泉小全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了一个新的生活,为自己和女儿枝丫带来了新的前景。
他坚信云芝会回来,这种信念使他保持了乐观和坚定。
整个故事强调了生活的不确定性,但也强调了坚持和家庭的价值。
泉小全不仅为自己努力,也为了女儿枝丫,克服困难,创造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总的来说,这个故事展示了人们在面临逆境时的坚强和希望,以及家庭的重要性。
它告诉我们,无论生活如何变化,坚持和努力都可以战胜困难,创造新的可能性。
这个故事深刻地探讨了家庭中的角色与情感之间的复杂关系。
云芝作为家庭的女主人,虽然没有对泉小全表现出深切的感情,但泉小全却一直为家庭努力工作和奉献。
然而,尽管泉小全的努力,云芝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家庭,抛弃了丈夫和孩子。
这个故事引发人们深思,关注了在家庭中,感情和责任之间的平衡问题。
它反映了个体与家庭之间的不稳定性,以及生活中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的一面。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即使面临困难和挫折,坚持自己的责任和价值观,也许会为未来创造更美好的机会,同时也反思了亲情、责任和家庭在生活中的重要性。